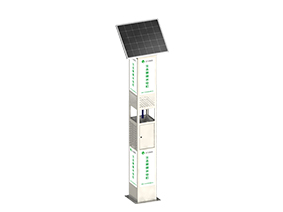错误。只要说一句话,人们就会感到害怕。“To bug”是烦扰、惹恼的隐喻。当有人“出错”时,他可能是在慌乱,也可能在赶紧逃离现场。也许你得了严重的“肠胃病毒”。飞翔、爬行、爬行、匆忙爬行、爬行、悬挂、荡荡、游泳的虫子。人们为什么愿意一辈子与这些生物保持密切接触?
事实证明,虫子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陌生。当然,它们可能有六条腿(甚至更多),但就像我们称之为家的这颗蓝色大理石上的万物一样,昆虫是我们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在进入细节之前,先把一件事弄清楚,就像黄夹克的毒针一样:当我们提到“虫子”这个词时,到底指的是什么?要回答这个问题,我们需要谈谈分类学,也就是生物的命名和分类。
基本上,“虫子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之一,随意地说:蛛形纲和昆虫。蛛形纲动物有四对腿,身体分为两节——比如蜘蛛、蝎子、螨虫或蜱虫。而昆虫则有三对腿,身体分为三个节段(头部、胸部和腹部)。也许再加上一对翅膀,你就能得到一只完整的昆虫。
昆虫和蛛形纲都属于节肢动物门,该门还包括一些我们称之为昆虫的其他动物,如蜈蚣、龙虾和螃蟹。在本文中,“虫子”大致指所有节肢动物,但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昆虫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自己在研究什么,就需要进入重点:为什么?
除了偶尔在家里看到蜘蛛或蟑螂外,你大概不会太多去想虫子。然而,它们在我们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——无论好坏——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越深,我们的生活就越有利。
内容
诡异的后果
与虫子共处的起伏
虫子很酷
诡异的后果

有些昆虫是有帮助的。例如,你可能知道蜜蜂数量正在减少,这对我们的食物链有严重影响。昆虫学家希望了解这一下降的原因和后果,因为这项免费授粉服务与我们的农业经济有着直接联系——金额达15亿美元[来源:霍尔德伦]。蜜蜂和其他昆虫负责为我们依赖的许多作物授粉,就像大多数坚果和水果一样。
另一方面,许多昆虫则导致农作物的破坏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昆虫啃食植物的果实、根系或身体造成的损害。例如,黄瓜甲虫的食欲是不分彼此的。成虫黄瓜甲虫会吃它们喜欢植物的果实、叶子、嫩芽和花朵,而它们的幼虫则喜欢啃食黄瓜的根。蚜虫等昆虫还可能将病毒、感染和疾病带入农作物,造成广泛的破坏。
更复杂的是,20世纪初我们开发了化学农药以减轻问题昆虫的破坏。但真正的问题是自我造成的:在消灭有害昆虫的同时,我们也消灭了有益的昆虫——就像化疗杀死癌细胞,但也会消灭健康细胞和组织一样。如果昆虫学家能学会有效针对有害害虫,有益昆虫有望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。
昆虫不仅仅是野外的问题。它们也会入侵储存的食物,在温馨的小麦仓里吃东西和/或筑巢,或者在你储藏室后面那盒被遗忘的Bisquik里。当然,虫子的兴趣并不限于素食者。有些吹蝇物种的当初几周生活在宿主的肉体中,以周围的肉为生。跳蚤和蜱虫可能导致贫血,而角蝇则以牛为目标,每天可消耗多达一品脱的血液。昆虫学家帮助我们理解昆虫的生命周期和行为,从而帮助我们保护自身的食物供应,预防食源性疾病。
与虫子共处的起伏
虫子可能会吃掉并伤害我们的食物,但我们可以反击——通过吃掉它们。也许你见过旅游频道主持人安德鲁·齐默恩飞往台北或厄瓜多尔,吃一些茧和蠕虫,无论是熟的还是生的蠕动。对于胆小的西方观众来说,这简直令人作呕。但从经济(和历史)角度来看,这很合理:昆虫无疑是丰富且营养丰富的蛋白质来源,然而几乎整个西方文明尚未普及。昆虫不是解决全球粮食短缺的万能办法,但它们是有效的补充剂。
虽然我们与昆虫和食物的关系一直显而易见,但我们与昆虫和疾病的关系却不然。疟疾在人类身上已有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历史,但直到1880年,一位名叫查尔斯·路易·阿方斯·拉韦兰的法国军医才在一名疟疾患者血液中发现寄生虫。十七年后,即1897年,一位名叫罗纳德·罗斯的英国军官成功证明蚊子传播疟疾寄生虫。有了确凿证据表明昆虫能携带疾病,对昆虫的迷恋不再是爱好;这是我们生存所必需的科学。
或者来个更性感的例子?你听说过接吻虫,也就是刺客虫吗?虽然所谓的“接吻病毒”有数十种,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本地种类可能携带查加斯病,每年导致50万人死亡,总共感染约000万人[资料来源: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,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]。查加斯病的传播实际上是“死亡之吻”:致命的寄生虫寄生在亲吻虫的消化系统中,进食后被虫子排出,通常在夜间靠近受害者的嘴巴。无意中的受害者可能会昏昏欲睡地擦拭或抓挠咬痕,将寄生虫引入血液中。如果不及时诊断,寄生虫可能会引起轻微、非特异性症状,如呕吐或腹泻,最终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,如心脏扩大或心脏骤停。仅就亲吻虫和查加斯病的地狱科幻故事而言,虫子绝对值得研究。
诺贝尔·施莫贝尔
有趣的是,罗纳德·罗斯因发现蚊子传播疟疾寄生虫而于1902年获得诺贝尔奖——早于当初发现疟疾是寄生虫的人。查尔斯·路易·阿方斯·拉韦兰因其工作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奖[来源:CDC]。
虫子很酷

说实话——虫子就是酷。我们为什么不想研究它们呢?
以白蚁群体的社会结构为例。白蚁群体按种姓组织,每个种姓都有其功能。你遇到的任何白蚁都是生殖、士兵或工蚁阶层的成员。无论白蚁是雄性还是雌性,无论是士兵还是工蚁,它都是无菌的。只有生殖阶层的成员才能做到这一点:繁衍后代。如果某个种姓人口过剩,白蚁会通过食人来恢复平衡。
但仅仅因为某件事酷而学习,往往不会吸引到科研资助。我们作为人类可以从自然科学中学到的重要教训是谦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,在昆虫领域很可能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。
想象一下在混凝土上钻孔:你身体前倾,试图用力对抗坚硬且不受欢迎的质量。这很难。那么,一只像羽毛一样轻盈的角尾蜂,怎么能如此轻易地钻进树木呢?为了弄清楚,昆虫学家们仔细观察了那条“角尾”。尾部实际上是两根针,通过“相互推开和加固,像拉链一样”缓缓进入木头“[来源:Goldenberg和Vance]。事实证明,这种设计理论上可以帮助宇航员钻入火星甚至小行星表面——在那里,利用体重无法有效,因为几乎没有重力。当昆虫学家研究昆虫世界时,他们可能会解决我们甚至不知道存在的问题。
尽管有些昆虫相当可怕,但绝大多数昆虫和蜘蛛对人类是有益的——或者至少,它们是无害的。据史密森学会称,“在任何时刻,大约有10万亿(10,000,000,000,000,000)个体昆虫存在。”新的估计显示,地球上每人对应超过000亿只昆虫。虽然这个数据可能会立刻让人联想到恐怖电影里蛆虫和成群的蚊子,但请放心:蝴蝶也是虫子,滚滚的蚊子和那些友好的小瓢虫也是。
重要的是,请放心,你比地球上比较大的虫子大好几倍。新西兰的巨型螽虫体长可达3英寸(7.62厘米),体重可达1.5盎司(42.5克)。虽然对虫子来说算大,但比普通鞋子或卷起来的报纸小得多。昆虫学家会确认,螽虫不会(也不会)把你的孩子带到中土世界,也不会把你活活吃掉。至少,可能不会。
作者的话: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虫子?
作为佐治亚大学的文科本科生,我被要求修两门科学课程:一门是“物理”学科,另一门是“生物”学科。大一学期我很兴奋地选了地质学课程,但我真的很害怕完成那门生物科学课程。我不确定当初是什么促使我选修昆虫学导论,但从头一天开始的每一节课都令人着迷。我依然是个终身的业余“虫子”爱好者,除非其中一只虫子爬到我身上。